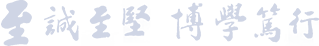报告时间:2013年5月10日
报告地点:文典阁
报告人: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汉学》副主编)
从课程上来说,国内授课方式与西方不完全一样。在德国有三种课型,分别是:演讲课、讨论课和练习课。所以,我希望在演讲过后与大家进行互动。
对于外语学院的同学来说,他们主要学习国外的语言和知识等,那么中国的相关知识与他们的关系便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可否认,德语系的同学通过了解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学习德语的重要的途径。但是,在跟西方人打交道时,他们问的多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问题,而不是欧洲的政治或德国的经济情况。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有一套关于中国的话语体系,即汉学。众所周知,掌握话语权,提升话语质量的前提是了解话语。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有密切关系,但并不是对等的。中国学术有其自身发展的固定的形态、阶段和区域。而汉学是在国外发展,虽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但汉学研究所使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西方的。
一、汉学研究线索
研究汉学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了解中国学术史。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例,我们可以研究近代史的档案和脉络等。而汉学研究则需了解近代史研究在海外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了解汉学家的生平、知识论的创新之处或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最重要的是揭示隐藏在汉学家背后的历史的或思想史的意义。另一条线索是,了解汉学家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原因。
下面为大家介绍两位学者:罗哲海、许里和。首先是波鸿鲁尔大学的教授罗哲海,他的一本书叫《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大家可以从书名看出两个概念,一是轴心时期,即雅斯贝尔斯对核心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在三个地域同时获得突破,分别是中国、古希腊、印度。在中国出现了“道”的概念,古希腊出现了“逻各斯”,印度出现了“梵天”。在这之前,基本上是实体性思维。罗哲海认为,儒家伦理所在的轴心时期对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概念是后习俗时期。这是美国的一位儿童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从儿童认知发展出的一套理论。他提出儿童认知最早时候属于前习俗时期,当孩子世界观形成后属于后习俗时期。他认为儒家伦理是后习俗时期的伦理,对整个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个汉学家在做中国文学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立场和观点是不同于大多中国学者的。
1、 关于问题意识
这完全是西方的问题意识,汉学家提到的所有问题是中国学者从自身研究出发很难想到的问题。关于批评角度,在域内或局部是不够的。宗教批判是宗教赖以生存的动力,如果没有宗教批判,那么宗教便不会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也不会长久存在。清初时期,整个中国跟西方世界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冲撞。中国的僧人和儒家知识分子开始攻击天主教。很多人认为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对佛教来说是大灾难,而一鸣禅师则说,若为抵攻佛教,佛教实非敌所能破。他清楚认识到基督教是不可能战胜佛教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基督教进入之后对于佛教是一个提醒,对佛法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刀不磨不利,钟不击不鸣”。来自外部的批判对于学术、宗教或思想来说是一种好处。
另一位是荷兰汉学家许里和,他最早做的是中国早期佛教研究。他的《佛教征服中国》等书在中国影响很大。他和许多汉学家一样,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读关于中国的书、中国哲学家自己写的书来认识中国。关于中国文化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反应,他找到了三个横截面,分别是佛教的传入,基督教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佛教传入中国后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一部分人极力反对佛教,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用一种宽阔的胸怀来接纳佛教,还有一部分人持一种无所谓态度。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外来文明冲击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特征。他认为中国文化面对外来冲击时最能表现出它的特质。如果从域内看具体则很难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很难看到三段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一个汉学家在认识中国时和中国学者间有很大的差别。
2、关于文本翻译
翻译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文本的翻译。罗哲海在2010年在北京开会时提到,国学没有前途,因为国学不涉及到翻译。翻译不是文本的被迫转换,转换文本实际上会产生新的问题的视角,会强化对名词的理解深度。如果不做翻译,那么拿到一个文本时则认为它理所当然是这样。而将文本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另外一种文字与文本间有种张力,这种张力往往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翻译问题对于汉学来说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讨论这类问题的出发点。如果大家从翻译角度讨论中国问题则会澄清很多概念,如“道”究竟是什么。如果不从翻译角度说,大家只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其他便不知。德文将三个“道”都翻译成一个词,这是不准确的。中国文化不是一种神秘的文化,只要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人是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的。第一个“道”表示存在者,第二个“道”是一种展现方式。存在是一种达不到的,不可以将其作为客观存在去认识的,因为存在主客体分裂。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将三个层面的“道”的意义理解并揭示出来,翻译仅仅是将你理解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翻译能够带来新的张力和视角,这是真正的讨论出发点。
二、汉学的认识误区
有学者说,sinology即汉学,在美国已经过时,我们没必要再谈论它。但是,美国并不代表西方世界,尽管其自认为代表着整个西方。在德文中,sinology依然在使用。在中国,“汉学”并不是一个过时的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定义。“汉学”非一时一地之学问,中国历史所涵盖的所有与中国相关的学问都是汉学。从拼写上看,sinology是拉丁语sino(中国)与希腊语logy(学问)结合的一个词,表示关于中国的学问。
1、 误区一:将汉学理解为关于汉族的、汉人的或古代知识的学问
近代以来,欧洲现代学科分类很清楚,如纽伦堡大学将汉学放入外国学中,他们将中国、埃及和整个伊斯兰的学问都放在汉学中。因为带有一定殖民色彩,所以他们不把中国哲学或历史分别放入哲学或历史系。
2、 误区二:汉学是中国学术在域外的延续
1923年,史学家陈垣在北大国学门的恳谈会上说道,要把汉学中心夺回到北平。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不了解汉学和中国学术本身之间的区别。汉学虽然研究对象是中国,但它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学问,它所使用的方法和研究本身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1937年到1938年间,北平的中德协会出版了关于50年来德国学术的一套书,其中有篇文章《50年来德国汉学的发展》提到,汉学是传统东方学的分支,是德国学术的一部分。因此,汉学是中国学术在域外的延续的说法欠妥。
三、汉学的定位
1、汉学的归属
于连的《迂回与进入》表明,中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为了更好了解古希腊的途径,因为中国会打破整个古希腊逻辑学和语文学,他可以回过头更好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他书里基本上看不到中国学术脉络。我们理解汉学家所认识的中国的过程是一个先“去脉络”再“脉络化”的过程,即把它放入新的语境中,产生在原来语境下所没有的、新的观点。因此,产生了归属关系的悖论。从逻辑上看,德国汉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下位概念,属于德国学术的一个上位概念。但是汉学本身不是一个学科,是一个学术领域,包括文史哲、宗教、语言等。如果将其作为学科看待,范围太窄了。所以,在归属方面产生了一些悖论。
个人认为,西方汉学系有其自己存在的理由,他们传授中国语言、文学基础等知识是必要的,但一定不是中国学术的一切。让一个汉学家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学者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将汉学系定位为语言和文学的基础,其他如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理所当然归类为历史系、哲学系、宗教系,而不是将其归为汉学系,否则,汉学研究很难深入下去。我们需要做的努力是让西方汉学系尤其是德国汉学系慢慢地把专业的汉学分离出来分别进入哲学系、历史系、文学系、经济系等,使中国学术研究更系统化,更深入。
2、汉学的划分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书写到,在东亚研究领域,美国人远比我们有优势,这不仅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设备和物质条件,更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合作意愿和开放思想。在德国高校,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以外的文化只是顺带得到关注,而在美国则是从两扇敞开的窗户往外看,一扇是穿过大西洋望向欧洲,另一扇是穿过太平洋望向亚洲,主要是中国。人们早就认识到,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及其文化的研究不能只在单一的学科内展开,而应该与欧洲语言文化划分方法一样,在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等学科中进行。就组织机构而言,大多数美国大学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美国这些观念是比较先进的。
我希望,欧洲汉学尤其德国汉学能够慢慢转入专业汉学领域中。按照近现代学术划分,欧洲很早就有了对中国学科的划分。德国早期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唐诗目录的研究,1829年在柏林藏书馆就有中国书库,中国书库是按照近代学科为分类标准,例如哲学、文学、宗教、语言等。在研究方法上,胡适曾经说过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是他的“娱乐”。这证明了我们应广泛学习知识。
如果汉学作为学术领域被看待,一方面我们是否有能力研究汉学。我曾做过关于中国哲学的翻译与研究,但汉学涉及到非常多的专业,缺乏相关专业素养,很难做整体汉学研究,目前能做到的只有对汉学学术史的梳理。另一方面是怎样还原历史语境。汉学家所做的研究是跟当时的社会、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必须还原到历史语境上,才能更好的理解,否则研究只能停留在表面,最重要的是揭示隐藏在汉学家研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国际汉语学创于1996年,但是到了2005年之后才开始慢慢转变,有了批判的文章,但真正能从思想史意义上揭示汉学家研究原本意义的文章还是很少。
四、中国的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对中国的研究,这个定义在慢慢转变。我们做海外汉学研究,实际上是对于西方人所做的中国研究的再研究,也就是对他们研究的批判式研究。这些年,海外汉学研究突然大热。最直接的原因是八十年代以后,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找寻自己的身份,开始重视外部世界的看法。另外一个原因是研究方法的突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研究已穷途末路,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都研究过很多次,如果没有大的考古发现,历史研究工作只是在不停的重复过去。但是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却对中国历史学的范式转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近代史按照后现代研究方式延续下来,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1、 中国对汉学史研究的原因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与汉学有着直接关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等以现代学术方法对中国学术史做的梳理工作,被认作是用西方方式梳理中国学术的典范。但是把它放在汉学的脉络下会发现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前已有三大卷相关书籍出版,所以用汉学脉络梳理中国学术史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所做的汉学研究并不是替洋人梳理历史,而是为了重建自己的学术史。
2、关于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
在1933年后,仅在北京就有100多位德国汉学家在各大高校做学术研究,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很多高校真正成为国际性学校。各种外国杂志在北京的创刊,为汉学著作提供了平台。很多刊物的水平之高,起到了典范作用。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学术“走出去”,并不是指地域上的走出国门,而是要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这可以通过和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著作以增强和国外的交流。民国时期中国的汉学研究是很繁荣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量汉学家和汉学著作流失,这是中国汉学研究的巨大损失。
对于汉学家来讲,真正的对手在中国。顾彬的《中国文学史》有三条主线:主体性、宗教性和忧郁。用三条主线把整个中国诗歌贯穿起来,这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少有人用。他曾做过神学研究,因此把宗教性加入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同时他也是一位诗人,梳理出“忧郁”这条在中国古诗脉络。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懂得利用东亚资源做研究,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加,使汉语逐渐国际化。许多汉学国际研讨会,都使用汉语。汉语已逐渐成为国际汉语学的通用语言。外国学者跟中国学者之间直接的交流,对外国学者来说很有意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影响深远。如今的汉语学研究、中国研究很难划分出局内局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做研究,中外汉学之间的区别会越来越小,这是汉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3、 汉学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基于当代问题的意识来做研究。第二,利用现代学术方法。国学、汉学都是阶段性的学术领域,以后会逐渐归类到具体学科里,如哲学、宗教、历史等。汉学家需要拥有国际化的视野,中国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同时汉学研究提升了中国学术的地位,使中国学术真正走向世界。第三,转化传统学术。传统的本身如果不经转化只是一堆僵化的历史资料,如能转化传统,我们将能从中汲取到很多养分。1982年,《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一书中提到:“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新的形式,从而达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未曾达到的目的。”用这句话证明中国文化的重构意味着,只有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有意义的潜能,以一种批判的意识对待传统,才能使传统具有应有的活力。
德国汉学和中国学术的发展最终会归结到与中国学术相关的领域,而非德国汉学的特点。1919年胡适自美回国后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谈到,中国文化若想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提出问题。以往中国文化的缺失在于没有真正的问题意识;第二步,输入学理,当时的中国缺少相关的理论来支持学术研究;第三步,整理国故,用西方先进的方式整理国故。因为国故中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 第四步,再造文明。既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又要以宽厚的胸怀接纳、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再造文明。
互动提问:
1、如何看待“汉语哲学”这个概念?为何要把西方哲学、汉语艺术和中国汉语研究产生的哲学著作放在同等的概念之中,这个概念和汉语研究产生的哲学著作有什么意义?
“汉语哲学”的提法是有意义的。“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哲学话语大多翻译自西方。但汉语有种西方语言所不具备的潜能。例如“本体论”、“汉学”等词与原先的英文、德文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汉语的创造性在于将外文翻译为汉语之后,翻译后的汉语本身具备一定的意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东方哲学的做法毫无意义,但他们却不知翻译成汉语的词有其新的意义。目前,该提法虽未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但必然会在以后发挥作用。
2、在讨论常态意义下的情况时,我们往往会忽略非常态意义下某些特质,那么当我们在讨论非常态意义下的情况时,是否会忽略常态意义下某些特质?
关于常态与非常态的问题。在非常态状态下,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别人。许里和并不是说只在非常态状态下观察中国文化,他还做了许多翻译和文本的研究。他的研究视角是对于常态的研究中国视角的补充。后现代的方法固然重要,但仅仅用后现代的方法去研究则会失之偏颇。常态的研究有很多,许里和截取非常态的断面做相关的补充,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
3、可能是由于翻译的问题,我们在读某些外国文学作品时感到味同嚼蜡。在中国著作对外传播、翻译的过程中能否去掉“漂白”的效应?
隋代一位和尚彦琮写的《辨证论》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是佛经不能翻译。他提倡让和尚们一进寺院就学梵语,唯此才能领悟释迦牟尼佛的原意。这种说法显然值得商榷,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不是学了外语就可以从事翻译事业,只有真正的翻译家才能从事翻译。有些翻译的东西是不尽如人意,但没有翻译也是不行的。在将世界文明中重要的著作翻译为汉语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日本在翻译方面做得很好,翻译在日本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在中国,唯有完善现有的学术体制,翻译工作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4、随着国际化的交流,德国汉学的特点逐渐减少。在1945年之后德国就进入了两德分裂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东德和西德的汉学研究分别有何特点?两者的关注点有何不同?
2005年我组织翻译的《历史人物与视角》中有几篇文章专门讨论两德汉学。东德汉学比较成熟,关注更多的是当代中国,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交流也未中断过。东德汉学的研究者也做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其他方面的研究,如中国的政治、能源等。西德没有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存在的。1945年后,西德只研究古代中国,在1968年之后特别是中德建交后才开始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
(本文由储有丽、李阳伸、徐晖、蔡丽丽经录音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